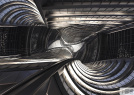(本文发表于2003年6月5日《北京晚报》)
在历史的谜题中追寻得深了,最终被它灼伤了心灵。
1994年,美国女作家雷瓦西在为郑和撰写的传记《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中叙述了自己在肯尼亚邂逅的传奇:一个黑人告诉雷瓦西,自己是中国人的子孙,是数百年前肯尼亚帕泰岛中国船遇难幸存者的后裔。1999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沿着雷瓦西指引的方向探访了肯尼亚拉穆(lamu)群岛中的帕泰(pate)岛,并提出大胆的推想:这些自称是中国后裔的人,很可能是郑和部下的后代。
这究竟是一个让人神往的艳丽传说,还是确凿无疑的历史真实?2003年4月3日,我们新华社电视采访小分队一行4人,奔向东非肯尼亚海滨的拉穆群岛,与肯尼亚考古专家一起,开始了为期6天的对历史谜题的追问。
一、阳光下耀眼的白色海滩
凌晨4点45分,星斗满天,我们乘坐的木船从拉穆群岛古老的拉穆镇起锚,划破寂静的黑夜,向远方的帕泰岛驶去。那些被我们的船头撞碎的波浪,向船头两边翻滚而去,因为得以折射星光的缘故,它们放射出一种神秘而美丽的荧光,仿佛一瞬间突然拥有了生命。在人类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能被人们记载下来并为今天的我们所知道、认识的事件也许就如这些被我们的船头撞碎而变幻为白色泡沫的浪花—虽然耀眼,然而微小;而历史不为人所知的其他部分,却如这黑暗中大海—如谜一样的深邃而寂静。
从拉穆镇到帕泰岛要经过一条狭长的海峡,海峡里的水很浅,只有涨潮的时候才能通船,这也就是我们不得不在凌晨4点45出发的原因。
在穿过海峡之后,天开始逐渐亮起来,在欣赏完海上日出的胜景之后,大约7点左右,船长儒奇指着远处的一片陆地告诉我们:“那便是传说中有中国人后代居住的帕泰岛。”
我们极目远望,想知道当年中国沉船的水手选择这个岛上岸的原因,但岛上一眼望不到边的红树林却阻挡了我们的视线—我们看不到岛上有任何的建筑或者炊烟。半个小时后,非洲的烈日已经开始煎烤我们的皮肤,帕泰岛也离我们越来越近,就在我们的正前方,我发现那无边的红树林突然有了一个缺口,阳光下,一片白色的沙滩闪烁着眩目的光芒,而且沙滩后面隐隐约越有房子的模样。陪同我们采访的英国剑桥大学博士、肯尼亚滨海考古专家齐里亚马指着那片白色的沙滩说:“那就是上家(shanga)海滩,传说中的中国沉船水手就是从那里上岸的。据当时记载,在1415年有一个长颈鹿从马林迪送给印度的国王,尔后由印度国王转送给中国皇帝,随后中国船队来到这里要带回更多的长颈鹿,结果有一条船在这里迷路沉了下去,船上的人从这边上家海滩上了岸,尔后住在这里和当地人开始通婚。”转过身,齐里亚马又把手指向了与上家遗址相反的方向,远方依稀可见几个小岛,“那里据说有一艘中国沉船,但我们现在并没有真正看到那只船。”如果真的有中国船只沉没在那片小岛旁的话,那么逃生的水手应该很容易发现上家村,因为上家村是帕泰岛上唯一一个面对着大海的村子,它正好与远方的那片小岛遥遥相对,而那耀眼的白色沙滩在绿色无边的红树林的映衬下,即使在数十公里外,也能够很容易地发现。
“扑通”一声打断了我们的沉思,船长儒奇熄灭了引擎并把锚扔下了海,“你们该下船了,从这里走到上家村。我的船不能够再往前了。”我们转头望去,发现我们现在位置距离那片白色的海滩还有600多米,莫非我们要扛着摄像机游过去不成。
原来,这正是拉穆群岛周围海域的特点:海水非常浅,而且密布珊瑚礁,科学家把这种地形称之为环礁湖地形,不熟悉地形的船只经常因为自认为距离海岸很远而搁浅,而拉穆群岛海域的另一个可怕之处是涨潮落潮之间海水深度差距非常大,每个月海水涨潮最深时与落潮最浅时竟相差9米—这湛蓝的海面对于古代没有声纳系统的木船来说,密布着杀机。
跳下水后,我们惊奇地发现海水果然只有齐腰深,经过半个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站在纯白的上家海滩。稍事休息后,我们在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驻帕泰岛工作人员穆罕迈德的率领下,向上家村遗址走去。上家村是帕泰岛上最古老的村子,建立于公元8世纪。传说中国水手上岸后想居住在这里,但当地人一开始并没有立刻接纳他们,在水手中的一位刀法出众的勇士杀死了当地一条为害多年的大莽蛇后,他们才得以在上家村定居下来。
据英国剑桥大学的考古专家考证,上家村在15世纪中期被焚毁,焚毁的原因可能是战乱和缺少淡水。即使中国水手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他们留下的痕迹也被当年的大火毁灭了。如今,上家村只剩下一片断垣残壁。而且,新的威胁也正在逼近上家村遗址:它即将被垃圾掩盖。
上家村遗址的最外围距离海滩仅有20多米,而这片海滩现在已经被一大片垃圾所占领。垃圾中以烂拖鞋为主,还包括破塑料以及各种能在海面上漂浮的东西。海岸边的红树林像一块巨大的海棉,在涨潮时把这些垃圾吸了进来。
“这些垃圾都是从印度漂过来的。”齐里亚马指着地上一只蓝色的烂拖鞋无可奈何地说。随着地球温室效应的加强,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上家村遗址这片传说中中国水手曾经繁衍生息的地方,将永远地被上升的海面带来的垃圾所掩埋—历史总是想法设法地运用一切手段来消灭它走过的痕迹。
穿行在上家村遗址中,我们向齐里亚马博士请教了“上家”这个名字的由来,和我们在肯尼亚遇到的所有地名相比,这个名字的斯瓦西里拼写看上去颇有些中国味道。
“shanga(上家,斯瓦西里语读音翻译为汉语拼音为shanggai)在斯瓦希里语中的原意是蜜蜂,上家村叫这个名字应该意思是‘有蜜蜂的地方’,另一种解释是shanga这个词来自于shanghai(上海),shanghai(上海)在中国 ,当时人们取这个名字是用来提示自己是从中国的那个地方来的。目前我们的在这里并没有发现蜜蜂,所以shanga(上家)来自于shanghai(上海)可能性更大,当然也可能是两种情况的结合。”齐里亚马博士对我们说。
激动与迷惑同时占据了我的心,如果“上家”的名字真的来源与于“上海”,那无疑是证实有中国人曾在此生存过的重要证据,但在中国人的发音中,“上家”与“上海”毕竟有着明显的不同,“上家”怎么会源自“上海”呢?
我把“上海”的英文拼写“shanghai”写在手上让为我们扛行礼的脚夫、当地居民桑巴告诉我它在斯瓦西语里的读音。
“shanggai”从桑巴嘴里吐出的声音让我感到惊奇,
“Just as same as the shanga?(和上家一样吗?)”
“yes.”桑巴肯定地点了点头。
原来在斯瓦西里语中,Shanghai(上海)中的h并不发音,因此“上家”的读音和“上海”完全一样。原来是这样。如果上家的名字真的来源于上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遇难的中国船只来自于中国元朝以后的时代—上海从唐朝起称为“华亭”,元朝统治者到1291年始建上海县,第二年春天,正式设立上海县。这正是郑和下西洋前100多年前的事情。
二、面向东北的墓碑
“你看,那有一只狮子。”齐里亚马博士在一处遗址前停下脚步,指着一块墙壁的最顶端对我说。我顺着他指的方向仔细地端详,那里确实有一个用珊瑚做的东西,而且与墙体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或许是我观看角度的原因,也或许是那“狮子”被风蚀和雨水冲刷得太久而失去了原来的形状,我不敢肯定那珊瑚就是一个趴在墙顶的狮子。
“那是人工故意做成狮子的,并不是完全天然的珊瑚的形状。”看到我迷惑的表情,帕泰岛的工作人员穆罕迈德补充了一句。在我的印象中,在房子的屋檐上用动物的雕像(一般是用螭的雕像,龙的一种)做装饰以及镇宅、辟邪之用,是中国古代建筑与众不同的特点,而现在,在东非海滨的一个毁于15世界中期的遗址上,我们竟然看到了一片墙顶上的一个狮子,这究竟是当地一个有创意的黑人工匠所为,还是获救的中国水手按照故乡的习惯用珊瑚雕刻的,我无法确定。但当地人显然只见过狮子,而根本不知道螭为何物,因而将螭与狮子混为一谈,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穆罕迈德的率领下,我们走出上家遗址,来到一块墓地。这块墓地的形状和中国农村最常见的那种墓地极为相似:前面一块石碑,后面是一个土丘。穆罕迈德认为这块墓地极有可能就是中国水手的墓地。
“按照当地的风俗,一般来讲,当地人都埋在村子里面,村子外面一般都是埋从外面来的人,所以我们猜想这是中国人的坟墓。”穆罕迈德指着墓地说。然而,最能证实死者身份的墓碑上面却没有一个字,无论是中国字还是阿拉伯文字。这墓碑并不是用石头做的,而是和上家村遗址的墙一样,用珊瑚混杂着从珊瑚里面烧制出来的石灰做成的。显然,要想在这种疏松而且充满着多孔的珊瑚的墓碑上刻字是非常艰难的,即使曾经有过字,现在也必定被数百年的岁月抹去了。
“几年前,我曾经亲眼见到过一块刻着中国字的墓碑,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找不到了,可能是被文物贩子偷走了。”穆罕迈德惋惜地说。拉穆群岛从9世纪起就成为了单桅帆船时代重要的贸易中转站,因此许多珍贵的文物散落在民间,这也就吸引了大量的文物贩子。
那块穆罕迈德曾经见过的刻着中国字的墓碑现在不知道在哪一个收藏家的柜子里,而对我们来说,一个真正能够证明中国水手达到过上家村,并有可能说明这些中国水手是否是郑和部下的证据就这样消失了。也许只有对整个上家村的墓地进行挖掘才能够得到相关的证据,但这却不是我们这些电视记者力所能及的事。
看着眼前这块被历史冲刷得满目疮夷的墓碑,我的心中突然荡起一丝悲凉,那墓碑面向着东北—那正是中国故乡的方向。我似乎突然看到了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抬起手,指着故乡的方向,盍上了双眼。而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国,他的父母妻儿,也曾哭干了眼泪,望断天涯。
三、“我的祖先来自中国”
离开了上家遗址,我们向着据说现在仍居住有中国水手后裔的西屿(siyu)村进发。西屿村在帕泰岛的西北端,上家村被焚毁后,大部分村民迁移到了那里,建立了西屿村。从上家遗址到西屿村7公里左右的路程,我们走了将近3个小时:在几乎没有树荫遮挡的情况下,非洲的烈日在头顶烧烤着我们的皮肤,40多度的高温让我们汗流浃背,脚下滚烫而柔软的沙地一边融化着我们的脚掌,一边竭尽所能的想留住我们的脚步,沙地中丛生的荆棘不断划伤我们的身体,肩膀上数十公斤重的电视设备和水、食物更让我们疲惫不堪。然而,事后我才明白,以追寻历史谜题所造成的心灵灼伤相比,这些都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到达西屿村时,远远就听见村中发出的喧闹声,好象在发生着什么事情。我们连忙寻着那声音赶了过去。在村中的一片空地上,不知什么原因,两个黑人青年正在打架,并且还动了刀子,出了血。但马上,两个小伙子都被人架走了,人群也开始逐渐散去。
不经意间,也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我转头向空地旁边一所房子前依然站着围观的人群望去,一瞬间,我感觉自己似乎被闪电击中,血管和神经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在那人群中有一个中年妇人正笑吟吟的看着我。她的皮肤比黑人要白得多,与其说她像是黑人,倒不如说她更像中国南方海边因日夜操劳、风吹雨打而被晒黑的普通的中国妇女,她脸上的笑容,更显露出一种典型的中国普通农村妇女的恬退隐忍的美。
“她是谁?”
“她叫巴拉卡·巴蒂·谢(baraka badi shee),她就是瓦上家(washanga)人。”穆罕迈德在我耳边轻轻地说。“瓦(wa)”在斯瓦西里语里是“从......地方来”的意思,“瓦上家人”的字面意思是从上家来的人,但在西屿村,“瓦上家人”则特指中国人的后代:当年从上家村迁来西屿村的其他人都被称为法茂人,他们是当地人与阿拉伯人以及葡萄牙人结合的后代,而独有中国人的后代被称呼为"瓦上家人"。
“我的祖先来自中国,当时到达上家村,和当地人结了婚,然后就不断延续下来了。”谢对我们说。
“你知道关于中国的什么事情吗?”我们紧接着问。
“不知道,但我很想知道,现在我也不断地打听关于中国的事情。”
在采访的间隙,我们注意到谢脚上的小拇指的指甲是不完整的—在中国民间,人们传说炎黄子孙的在身体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脚上小拇指的指甲分成两半。谢的家里唯一与中国有关的东西是一个中国的搪瓷盆,丰收牌的,看着上面的花纹估计已是20多年前的产品,但现在依旧是完好如新。谢有5个孩子,她的小女儿瓦玛卡现在正在拉穆镇上高中,明年就将考大学。
“我想到中国上大学,因为我的祖先来自那里,而且中国的地位也比其他很多国家高。”瓦玛卡对我们说。
“你想在中国学什么?”
“学医,这样当我的家人生病的时候我可以帮他们看病。”
瓦玛卡与她的母亲相比更像黑人—谢的丈夫是当地的法茂人,但她的皮肤仍然较当地黑人要白许多。
为了证实谢关于自己是中国人后代的说法,我们采访了西屿村的前村长、60岁的奥玛尔。在这个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地方,关于村子的历史是由历任的村长口口相传继承下来的。
“瓦上家人的故事是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据说他们来自中国,很久很久以前,一艘中国遇难船只的幸存者到达这里,和当地人融合了,后来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些人有漂亮的头发,大大的耳朵,他们没有其它名字,就叫瓦上家。”谈到中国人的事情,老村长显得很激动。“瓦上家人不少,但他们都属于一个叫做穆罕穆德·谢的家族。”“穆罕穆德”是阿拉伯人的姓名中最普通的一个,因此许多非阿拉伯血统的人在皈依伊斯兰教后都把自己的名字加上一个“穆罕穆德”,以作为伊斯兰教徒的标志,而“shee”的斯瓦西里读音则与中国的“谢”完全一样,它是否来自于中国?但巴拉卡·巴蒂·谢对此一无所知。
我再次向脚夫桑巴请教了这个问题,他说“shee”肯定不是肯尼亚当地人的姓,他也从未听说过有任何的穆斯林叫这个姓。“这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姓。”桑巴反复咀嚼着“shee”的读音,摇着头说。
“谢有兄妹6个,除了她以外,她的其他兄弟姐妹都已经离开了西屿村,居住在拉穆镇和蒙巴萨、马林迪等地,”穆罕迈德向我们介绍说,“西屿村现在还有4户瓦上家人,大概20人左右吧。”
在拉穆镇,我们见到了穆罕迈德向我们提起的谢的妹妹泰玛,当我们正在采访她的时候,不知是谁在镇上散布了我们来采访的消息,不到一会就又从远处赶来了两对母女。
“我们都姓穆罕穆德·谢,”这两对母女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是来自西屿村的瓦上家人,我们都中国人的后代。”
“那你们之间经常联系吗?”
“是的,我们经常联系,经常来往,尤其家里有什么大事的时候。”
不管他们是不是中国人的后代,中国这个称呼已使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为了方便我们的拍摄,在两个母亲的要求下,她们年轻的女儿解开了一直蒙在脸上的面纱—对于传统的穆斯林来说,这是她们最亲密的亲人才享有的特权。
这几个瓦上家人还告诉我们,除了西屿村和拉穆镇以外,瓦上家人在蒙巴萨还有100多个,有的甚至去了肯尼亚的内地。
如果瓦上家人真的是中国人的后裔的话,那么现在中国人的血脉已经在肯尼亚甚至是广袤的非洲大地上散布开来了。
四、如虚如幻的历史残片
“我们这个岛上曾经有过繁荣的制丝业,”老村长奥玛尔在接受我们采访时神秘地说,“但是在几十年前,突然中断了?”
“为什么中断了?”我们对奥玛尔的话感到震惊。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因为会这个手艺的人都死了。”
“那么你们拿什么制丝呢?”我们接着问。
“原料来自索马里,但是我们这个岛上也曾经养过蚕。”
“养蚕?这是真的吗?”我们的心几乎都提到了嗓子眼。
“是的,但只是在一年的某个时期”这简直太神奇了,神奇到我们几乎无法相信。养蚕制丝是中国人的专利,虽然公元5世纪一位罗马传教士将蚕种藏在手杖里带回了欧洲,但1498年达·伽马率领由三只帆船的船队到达东非,他们只带去了一些简陋的小珠子、铃铛和洗脸盆羊毛和酒----这曾经让非洲人很鄙夷。而先于欧洲人70年到达东非的郑和却满载着丝织品、瓷器、茶叶等中华宝物,郑和的船队更载有各种技术工人。难道西屿村的养蚕制丝技术就是郑和部下的后代传给当地人的吗?
但线索再一次断了,由于制丝业在数十年前的突然消失,我们无法亲眼见证和比较西屿村的养蚕制丝业与中国的技术之间的异同。
“您听说过中国船从这里带走长颈鹿的故事吗?”我们又向奥玛尔提出一个问题。
“这也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但不是从这里带走的长颈鹿,而是从马林迪。”奥玛尔回答说。奥玛尔的答案为我们考证在上家村定居下来的中国水手是否是郑和的部下带来了一线光明。据史料记载,1419年,郑和船队带着非洲麻林国(即现在肯尼亚的马林迪)进贡的麒麟回到中国,引起轰动。而这麒麟便是长颈鹿。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名为麒麟图的明朝的画,画的就是长颈鹿。而这个史实,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也鲜有人知,更何况是非洲偏僻小村庄里的一位老人。最大的可能就是沉没的中国船只的幸存者告诉了当地人关于从非洲带回长颈鹿的故事—当时郑和远航东非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长颈鹿这种被认为是麒麟的动物。另外,传说中国水手是在上家海滩登陆并定居于上家村,而上家村毁于15世纪中期—几乎就在郑和船队到达东非后20多年后,将这两条线索综合起来:如果曾有遇难船只的中国水手达到上家村并告诉当地人关于长颈鹿的故事的话,那么极大的可能那些幸存的水手就是郑和的部下。
然而这只是推理,我们没有切实的证据来证明郑和船队中的一条船曾经在上家海域沉没。能够作为重要证据的齐里亚马博士曾提到过的那艘中国沉船现在依然静静地躺在海里,幽深的海水掩盖着它的真实面孔。
“沉船的位置大约在距上家海岸70公里的地方。据那些去深海打渔的人说,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艘中国沉船,并在那个地方打捞上了一个中国陶罐。”在从西屿村返回的路上,齐里亚马教授在地图上指给我们看沉船的位置,“如果中国政府能派遣科学家来帮助我们确定沉船的位置,我们会非常高兴,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船上都装载了什么货物,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发现中国和东非的历史渊源。”
在我们的要求下,博士带着我们去参观了那个被捞起来的陶罐。去年11月,一个捞龙虾的当地渔民在海面下55米的地方捞起了这个陶罐,并随后把它卖给了居住在拉穆岛仙拉镇的古董商人兼瑜珈修炼者、英国人特勒。
当我们在特勒家院子的一个角落里看到这个陶罐时,我们认为它更应该叫做陶瓮:它有70多厘米高,最粗的地方直径有将近50厘米。这是一个六耳陶瓮,但有5个耳都已经不在了。将陶瓮翻转过来,我们想从它的底部发现一些关于它的制造年代和制造地点的暗示,却发现由于这个陶瓮长期呆在海底,底部已经被各种海生物建造的巢穴掩盖。但从陶瓮上栩栩如生的双龙戏珠图案可以判断,这确实是中国的产品,只是具体年代,我们无法考证,只能留待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在东非海岸打捞出来的第一个完整的中国罐子,以前在这一地区仅仅发现过碎片,从考古的角度来说这是第一个完整的。”齐里亚马博士同时认为这个陶瓮不是用来贸易的商品,因为制作比较粗糙,“它应该是船上水手使用的罐子。”在我们采访结束的时候,也许是真正认识到了这个陶瓮的价值,特勒指挥家里的黑人把陶瓮挪到屋里去了。现在,这个陶瓮对于特勒而言也许意味着一大笔财富,但对我们来说,它依然解决不了我们的历史谜题
—这个罐子无法证明它来自于一艘中国沉船,更无法证明来自郑和的船队。
在中国的唐代,中国的许多城市就已经具有了国际化的特点: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学者或乘坐帆船或沿着丝绸之路到达并居住在这些城市中,中国的广州、杭州等城市的港口里停放的大型海船更往来于世界各地。史料记载,公元7世纪时的广州已经居住着2万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每年往来的大型商船更是不计其数。很难确定是一艘中国船还是一艘阿拉伯的商船在中国补充了一些船上用品和货物以后沉没在了拉穆群岛附近——阿拉伯商人从公元8世纪起就往返与东非和中国之间进行贸易,元朝时的旅行家汪大渊就是乘坐阿拉伯的商船到达非洲的。
我们的采访到这里似乎一无所获:历史在它前进的路上毁灭了大部分的确凿证据,却留下美丽的传说和支离破碎、如虚如幻的历史残片来诱惑我们,我们仿佛被历史玩弄于股掌之上,却无法自拔。
尽管我们剪下了瓦上家人巴拉卡·巴蒂·谢的一缕头发,准备回国后请基因学家根据她的基因来判断与与中国人的联系,但这也许也是枉费心机:郑和的船队中本身就有许多是回族—阿拉伯人的后裔;而且,郑和为了远航非洲,特地请了许多善于航海的阿拉伯人作为向导,如果巴拉卡.巴蒂.谢恰好是这些人的后代,基因就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另外,从拉穆群岛当地人的风俗来看,600年的时间已经足够繁衍30代,而拉穆群岛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各民族大融合之地:阿拉伯人、印度人、欧洲人的血脉在这里相互搀杂,如果真有中国人的基因,那么这些基因也不断与其他种族的基因纠缠在一起。现在,仅存的那些基因片段还能否说明问题?
看来,真正能够解决是否有中国沉船的幸存者在拉穆群岛留下后代以及这艘中国沉船是否是郑和船队中的一艘这些历史谜题的答案依旧深埋在上家遗址的墓穴中,依旧静静地躺在深不可测的海底。
五、心灵被历史的谜题灼伤
在采访结束后,我们返回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我们乘坐的双引擎螺旋桨飞机在气流的冲击下起起落落,我的心情也渐渐的沉重起来:似乎是被飞机突然的动作所激荡,羞愧从心底慢慢地浮上来。对于郑和这个曾经让世界惊奇的中国人来说,我们了解他的脚步已远远落后了。
我们新华社的电视采访小组虽然是国内第一批到达肯尼亚拉穆群岛进行采访的电视记者,但我们至少已落后海外媒体的记者9年的时间:1994年雷瓦西首先访问了这里,随后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尼古拉斯,然后是台湾和新加坡记者,最后才是跚跚来迟的大陆记者。而更让我欲哭无泪的不仅仅是我们这次探寻拉穆群岛的郑和部下的后代没有得到答案,更是因为另外一个让人痴迷却也许永远没有答案的历史谜题:为什么郑和在到达非洲以后没有继续向前,去达到欧洲和发现美洲。以郑和船队的实力—郑和船队由300艘船、28000人组成,最大的船有44丈4尺长(约合151米多)、18丈宽(约合61米多),这即使是在郑和以后500年内也依然是世界最伟大的船队—当时的中国人应该能够轻而易举地首先发现美洲而不是仅仅率领了3条破船、90个水手组成的船队的哥伦布,它的船队中最大的船只有30多米。
然而郑和的远航本来就不象哥伦布那样具有发现新大陆的目的。郑和远航的最大目的是展示中国皇帝的威仪,以使四方“蛮夷”臣服于中国皇帝的强大与慷慨—“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另外一个目的则是去发现被朱棣篡位后下落不明的建文帝的行踪。因此,郑和七次下西洋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只是是给皇帝带来满船“无名宝物”—从大象到观音竹,从麒麟到香料以及明朝政府无法承担的巨大支出。于是,朱棣之后的明朝皇帝和大臣们开始对郑和远航的实际意义产生了怀疑:“三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回,于国家何益?”
于是,当西方船队绕过好望角到达亚洲、当西班牙水手哥伦布在寻找新大陆的航行中发现美洲的时候,中国开始实施“海禁”。郑和船队的船员被遣散,船只任之搁置废烂,航海图被兵部尚书刘大夏焚毁。此后,明、清两朝中国不曾有过任何出海之举。这最终使早已掌握了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的中国失去了参与15~16世纪之交世界地理大发现并随之成为世界强国的机会。
郑和七下西洋不过百多年后,中国东南沿海即受日本倭寇蹂躏,澳门更落入葡萄牙人之手。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在具有威加海内、臣服天下的实力和机会的时候却突然缩回了自己触角。他们的解释是:中国不够贪婪,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更视商贾为“小人”。古代的中国关注许多事情:荣誉、文化、艺术、教育、祖先、宗教和孝顺父母,但如何赚钱却不在行列之中。另外,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的自我满足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人认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天下都是自己的,又何必去征服。
相比而言,欧洲是贪婪的,葡萄牙因为渴望香料和其他珍贵的日用品而领导了15世纪的探险热潮,利益驱使着他们将船驶得更远:不仅到达了非洲海岸,甚至绕过合恩角到达亚洲。他们获得的利润是巨大的:麦哲伦的船队曾经从一条船装载的26吨丁香中赚取了1万倍的利润。
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尼古拉斯在他的报道中这样写到:“假如旧中国永不厌足,胸怀四海,其它的贸易商紧随郑和行踪奔向海洋,亚洲很可能已主宰非洲,甚至欧洲。假如,郑和航海到了美洲,历史将如何改写?其影响所及简直无从想象。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纽约时报》将以中文发行。”
这是让所有西方人沉醉的历史谜题,但却灼伤了我的心灵,仿佛被一根600年前埋下的刺深深地扎了一下,鲜血开始一点一点地流出来,吮吸自己的鲜血也许是避免再次受伤的最好途径。
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它所著的《全球通史》中这样写到:“尽管郑和的远征确切地表明,中国人拥有控制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他们却自愿地撤退了。蒙古统治结束后,明朝的中国人将自己与外世隔绝。中国人将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转向内部,从而自愿放弃了在欧亚大陆……”
历史如谜,如虚如幻;历史如镜,亦梦亦真。(费茂华)